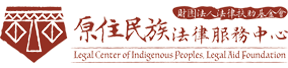最新消息內頁
活動訊息
最 新消息
News
【專題演講】
主講人:李建良教授(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主題:原住民土地法制的法治圖像
講者首先提及,關於原住民土地法制問題的思考邏輯,我們從人、事、時、地、物五個方向來做思索,而這五個方向是交互相關聯,就原住民的土地除了陸域之外,也應該關注水域以及海域,回歸到主題法治圖像,整個原住民土地的法律問題,牽扯到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互動關係,應該是一個協力關係,但仍有相互制衡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將以宏觀的方式討論可能遇到的問題。
從立法定義來說,法規主體中的原住民、原住民族,除了由立法機關規定、行政機關核定外,近期也有憲法裁判上的身分界定,而人是土地的核心,不管是原住民或是原住民族的認定,憲法裁判將會是未來的方向。以原住民或原住民族作為法制核心的立法,不應該只以原住民或原住民族作為名稱才算與原住民(族)相關的立法,實際上原住民族法制的立法坐落在各法之中,這才是今日所要探討的核心,而原民土地的法制元素有不同用語,如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地區、海域等等,延伸的思維為三種不同的概念,分別是「法律創設制度」、「現行事實的狀態」、「行政機關核定的區域」,而三種概念下的原住民族土地,其究竟關係是什麼,還有待我們去討論。
原住民族基本法(原基法)第19條中規定的土地,除了原住民族地區外,還包含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似是土地與海域相分割,但就原住民傳統文化而言,海域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息息相關不可分割時,此立法是否妥適不無疑問,參考國土計畫法的規定未有此區分,未來或許可以考量不需如此分割立法。此外,原基法第19條的「容許行為」,規定的並不清楚,何謂「依法的非營利行為」?又區分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重點並非是否為營利行為,而是仍當以「傳統文化、祭儀」為核心,此立法是否妥適不無討論空間。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1項有關諮商同意的規定,所討論的需行諮商同意的行為,在實務上如工程修繕有沒有涵蓋在這規定的範圍內?因為工程修繕非新的土地開發而是既有工程的修繕,此外,關於本項的「保護機制」,沒有經過原住民同意的處分雖無效,但回過頭來,思考本項的「保護機制」包含諮商同意、諮商參與、利益分享,卻都以「或」來相區隔,此多種選項的規範在具體適用上須仰賴授權的諮商同意參與辦法,此項規定不夠具體在實務運作上是否會造成問題不無疑問?而同條第2項的參與與損失補償之保護機制,關於參與的規定不足,損失補償則為立法者所為之特別規定,與憲法下所賦予的特別犧牲之概念不同。
原基法第21條第4項所授權的諮商取得原住民部落同意參與辦法(諮商辦法),由原基法第21條來看,最終的決定機制應該歸於部落會議,立意良善,但在實際運作的個案中仍生有爭議,反而權利淪落到行政權,司法機關有多大的裁判空間也是個問題,當問題產生時究竟該訴諸行政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這取決於立法單位。
另外就是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我們需要特別強調,原住民族土地關係各原住民族彼此間的相處,非單單法律問題。
原民土地法制中是否存在特別法呢?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4條第2項的規定,又或是森林法第15條第4項,但規定在實務上適用上卻又發生問題,如森林法中所規定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是否只限單一原住民族?而不包含其他原住民族?即是所謂的「屬人效力」?
原住民保留地的規範光譜與放射效力,放在三個角度來思考,是制度性保障、還是集體性的權利?又或是保障個人權利?從原住民保留地的歷史來看,此涉及歷史因素、制度性規定,原則上屬於公有地卻又可在一定條件下私有,隱含的問題是說,原住民保留地究竟是集體權的保障,還是個人權利的保護?另外就是原住民保留地移轉限制的問題,移轉以原住民為限,憲法法庭宣告原保地借名登記無效,只能移轉給原住民,但憲法法庭成立的論據應該是原住民保留地轉給個人後土地用途有所限定,但原住民保留地的用途是否有必要如此限定?而討論野生動物獵捕區域時,大法官釋字第803號解釋給予行政機關相當大的空間。
關於法制的反思,首先是原住民保留地,它是一種制度,有其歷史背景,但原住民族保留地,仍然存在未經登記但仍然由原住民繼續使用的原民土地,那究竟該如何認定?該如何處理?原住民保留地不該依附於山保條例,應當獨立出來,正式將原住民保留地入法,才能凸顯原住民的主體性。就原民土地上的行為規範,當傳統規範與國家規範不同發生衝突時,究竟該如何解決,如何去看待?「表面上的規定看似保護原住民,實際上卻反而讓原住民權利更為限制」。